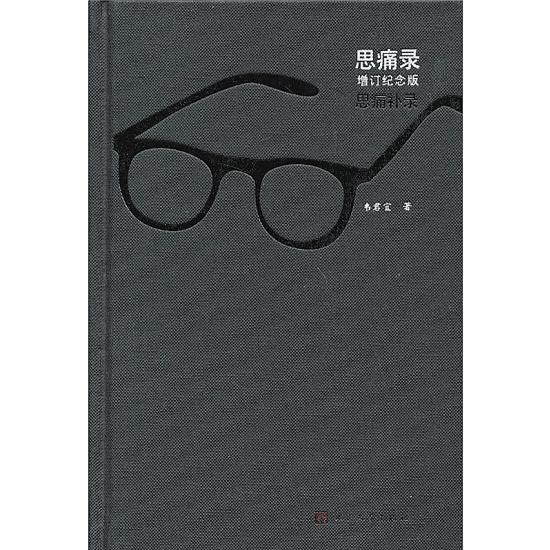干校劳动的回忆
到9月(注:1969年)底,国庆节前两天,打发我们到湖北咸宁干校去劳动。所谓“干校”,实系永无毕业期限的学校,只有“干活”一门课的学校。直到这时,一般革命群众跟我们一起下干校,他们才有点明白自己跟随造反的结果是什么。当然,一开始大家都还认为是下去革命的,也不知道此去的前途是不准回来,等 于流放。
我们到达了咸宁一块湖区,住在老百姓家里,自己先盖房。我们社(改名为连) 的全体妇女集中住在老乡的牛棚里,满屋牛粪味。工作首先是自己和泥做砖盖房,钉竹条搭棚做仓库,准备将来把湖里的水放干了种稻子,自己取名为“向阳湖”。我记得破土动工的第一天,大家倒也挺有点新鲜劲的。一个女秘书,干完了一天 活,回来发表感想说:“我这才觉得我这个人一天干了活,不是白吃饭。以前我们 成天干什么了?”她大概觉得自己的半生就是白吃饭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中年编 辑,手持利斧,踏着竹条做的架子,凌空大步砍竹头,脸上毫无惧色。我的任务是和 舒芜一起挖一个坑,修建临时厕所。我们两人累得大汗淋漓,才挖好了,欣赏欣赏,边也修光了。但是,一会儿上级传来命令,厕所要挖在另外的地方,我们只能搬家,还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凭吊了一番。这时候才有点明白“上边歪歪嘴,下边跑断腿”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们干,真的拼命干。一般的群众,在大家差不多的环境下,不再那样歧视我们这群牛鬼蛇神。但是,仍然有一些自视身份比别人高的人,用语言和表情来伤害别人,以此娱乐。我记得的,研究鲁迅的杨雾云(是鲁迅的朋友),因为素无干力气活的习惯,铲土只能一次小半铲,就被我们连队那位首先解放的首任指导员取了一个绰号,叫“二两半”。然后,在一次大会上,由取绰号者向人提出讥笑的疑问:“还有这么一位‘二两半’,真把那点儿土算计得准,为什么非得二两半,再多铲半两,来个三两,就一定不行? ”我没有看杨雾云先生的脸,因为这时候我不忍去看。他有什么罪? 大概就是早年认识鲁迅的罪吧? 而这时正是把鲁迅捧成毛主席以下第二大神的时候。
我们拼命干,多么希望得到人家一点点称赞,至少是同情。哪怕是来自非革命群众的。我记得有一次挖土,我是牛鬼蛇神们的临时组长。诗人陈迩冬也是向无多少劳动习惯的,这时他却一铲一堆,一铲一推,一连许多铲,头上流着汗。我轻轻无意地说了一句:“陈迩冬今天干得不坏啊。”只见他脸上突现不好意思的谦虚之状,擦了一把汗,像小孩子得到大人夸奖似的说: “不过……不过还是有点疲劳啊 !”其实,我并未想到这句话在这里能给他以安慰,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多么容易得到安慰和满足的啊,而所得却如此吝啬……
我得到的待遇也是一样。开始时,每次劳动间歇就“开斗争会”,毫无目的地乱骂一通。后来,大约由于这样的“斗争”实在妨碍群众的休息,才取消掉了。平时,我挑不动砖时就用胸顶着上。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地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后来,日久天长,劳动成了每个人的本分,既不觉得光荣,也不觉得受苦——除了太累的时候以外。我记得在秋天挖泥做砖时,下午小休。这时已经取消了我的挨斗供娱乐的任务,可以休息了。满地都是供和泥用的干稻草,天上是暖融融的秋日太阳。我就找了一个附近没有人的大草堆,伸脚躺下,仰望蓝天,真比盖被子还要暖和,比睡在大玻璃窗下还要敞亮,一下子就让我脱离了这个受苦受难的人的世界,躺在了地母的怀里。
第二年我们要秋收,用大量的稻草,在湖田中心搭了一个休息棚。那里又凉快,又四面来风,旁边连(中华书局)的“战友”们走过,跷着手指说:“真是文学出版社的杜甫草堂啊!”
类此草棚闲话,只要我们把自己当时身受的政治待遇忘掉,也未尝不可以怡情悦性,物我两忘。后来我们就这样过日子。
抹不去的记忆——忆向阳湖畔十个无罪者
人们的记忆多么容易抹去,记忆力又多么差啊。在“文革”前还没有上中学的我们的儿女、侄儿,现在成天谈的已经都是深圳怎么赚钱,上海怎么炒股,谁又当上了经理了,没有再提起他们自己曾经在向阳湖边度过的童年和少年。
可是我的记忆怎么能抹去呢?——那把我的中年时代剥夺掉,把我推入了老年的向阳湖。湖北咸宁农村的一块水沟,原来不存在这么一个“湖”的沼泽地,被我们流汗开垦成田的向阳湖。我们在这里被驱赶、被改造,使我们悲痛,又使我们深深铭刻在心的向阳湖。
当年我们一起来到向阳湖,我们这个不过二百多人的小小单位,竟有八个埋骨在这里。其它单位(连队)也有。加上邻居中很熟悉的两个,我记下了十个完全无罪的葬身于此的人的名字。原本人是个活着回去的“走资派”。
我忘不了他们,一个一个数一遍吧。不论其生平成就高低或有无成就,他们和我是一块儿被赶到这里来“锻炼”的。
头一个死在这里的,是瘦瘦的挺本分的公勤人员老艾。他在社里一向做公勤各行工作,还当电工,常见他擦地板抹玻璃,与什么“黑帮”也沾不上边,本人就是工农,也没有必要再来接受工农的“再教育”。可是我们单位当权的——不知是“造反派”还是“军宣队”,却决定除了留守机关的响当当“革命派”之外,一律下乡改造。老艾大概是觉着应当在缺少人力的干校里出一把力,自愿参加了下干校的队伍。
他身体本来不好。刚到,活儿多,据说那晚他去收拾刚搬来的锅炉,没有人帮忙,他一个人使劲扛,不知怎么一来,他就倒在锅炉跟前了。当我知道消息时,他已经断了气。他身后遗下了靠他生活的妻子和一儿三女。当时他的儿子不过是几岁的娃娃,小女儿在上小学,跟着他的在机关做临时工的妻子一起被编入我们大家都怕得要死的连队,天天可以和我们一起打饭,真是只吃一口饭。后来他妻子和我住同屋,听说我女儿被赶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每月拿二十八元,她曾叹气说:“我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多好。”当时我就明白了我们所遭遇的不幸,在她的生活经历里这并不算是不幸。还有更多的不幸在等着这位自强的母亲。
第二个死去的是期刊发行科的科员周玉祥。他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走资派。只因所有的文学期刊全停办了,他已经没有业务,于是也被送来向阳湖当革命群众。他在家乡种过地,在这里也挺努力地种地。他对待我们“走资派”态度平等,有时也忘了我是走资派,跟我聊天。说起这个地方的图书市场,说咱们的期刊在这里准有办法发得出去。他有好多主意。我才发现自己太官僚主义,这个干部是个很钻研业务的人,将来我若有出头之日,一定应该想办法用上这个人。可是,一切都晚了。他病了一场,据说并不是重病,可这里没有像样的医生,始终也没有弄清是什么病,头天晚上还没事,第二天一早就糊里糊涂里离开了人间。也是一家人靠着他一个。女儿号哭着赶来奔丧求告,别人也是送给她一点无用的同情。
第三个是女校对程穗,是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赶到向阳湖,老是解放不了。只因她年轻时在重庆当过小职员。那时国民党叫所有小职员都必须登记参加国民党,她听话登记了。在她的登记表上有“监察员”三个字。现在我们的造反派要她坦白交待这一段“反革命历史”,可怜她磕头求告的,把那一段生孩子、找职业和一切生活琐事都详细讲了,甚至说自己是宣传委员、什么委员都胡诌到了,就硬是交代不出这“监察员”三个字来。于是她受尽了谩骂,包括“走资派”和“解放”不了的人带来的孩子们,谁愿意打她都可以任意打几下。她成了所有“地富反坏右”里边最下层的人,去上工的路上,一路挨打、挨骂。我曾和她编在一组,在挨斗人“小组会”上,我再三劝过她:“你有什么可交代的,不管是大是小,赶快说了算了吧,你不会有多大事。”她只是掉眼泪,说:“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什么。”现在看来,可能她根本就没有当上这个并不大的官。就这样苦熬到连我这个“走资派”“解放”了,她却还在继续受苦。终于她下决心离开这个受苦的人间,先是服毒,想不到又遇救。后来终于一口饭不吃,给她饭她偷偷吐掉,活活绝食而死。
第四个是刘敏如,古典编辑部的秘书,是个胖子,血压挺高。社里都知道他这个秘书与众不同,别的编辑部都是由编辑负责和作家联系、写信,讨论稿件处理问题,只有古典部的编辑可以只看稿,发表意见。那些写信联系商量的事,都由秘书刘敏如包了,包得漂亮,别部的秘书比不了。就这么个人,却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遣来向阳湖。原因是他那个家乡曾是日本占领军与八路军双方争夺的地区,是两面政权。他在本乡当小学校长,由八路军这边委任他当了地下村长,日伪军那边去也要一个村长,老乡们认为一客不烦二主,也归他去应付。就这么一回事,却被“造反派”打成了汉奸,再怎么也说不清。于是他被揪来了,跟着人们去下地,因为是“历史反革命”,有病不予照顾。记得那是三伏天,按武汉一带的规矩是早晨上班中午午休到晚上,再上一会儿班。可有一个大热天,北方来的造反派不听这一套,还叫他整天下地。刘敏如在弯腰锄地的当口,跤跌在地里,再也叫不醒,不知道是中了暑还是脑溢血,反正就这么一声不响地完了。大热天死人不能久停,“造反派”们作了主,就把他就地埋在那块土地里了,没有立坟头,他家的人来也找不着。
第五个是谢思洁,这一位原是出版社现代编辑部的出色人物,看稿发稿是一把手,和社外叫得响的编辑名家们都是有来有往的,和郭沫若郭老也挺熟。毛病就出在他年轻时候,本来是共青团员,被国民党抓去了,他没有否认这个团员身份。十八的孩子,还不知怎么表白气节。他爸爸是个资本家,是拿钱把他赎出来的。他从此失去了组织关系。后来他没有做国民**,由他父亲想法在一家公司里找了个差事。他却仍然靠近进步组织,这才认识了郭老,也认识了一些文人。他在公司里一直干到解放。爸爸给他一些钱。他还惦记着文学事业,就从公司职员改行当了编辑。到了文化大革命,年轻时那件事被翻了出来,被造反派们定为叛徒。他急忙把爸爸的钱全部献出,但是不中用。爸爸给的钱又连累他成了资本家、阶级异己分子,当然他也被赶到向阳湖来改造。改造了一阵,得了癌症,不准回北京去治,给送到武汉。他躺在病床上,还写信来,还叙说生平的苦况,和一片忠心。信尾署着“谢思洁伏枕上言”。当文人当苦了,他还嘱咐女儿不可嫁给文人,要老实生活。但是说什么也已无用,人是不能救了。这个人就此死在了武汉。
第六个孙昌雯,女校对。下向阳湖时还是革命群众。她丈夫是古典文学编辑,虽算不得“造反派”,也还没有被打倒,夫妻俩一起带着两个女儿来的。没想到来了以后不久,“造反派”们忽然发现了孙昌雯和另外一个女校对在北京时,曾有过破坏江青伟大形象的言论和活动,后来听说,大概是说了江青年轻时当电影明星跟几个男人结过婚的风流韵事,还传看过照片。这下子了不得,她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白天审,黑夜逼,要她招供出主谋的反革命来。大冷天要她在院子里罚站,一站站半夜,她本来身体不好,就此弄出了一身重病,终至起不来。她自己干不了活不说,还得拖累丈夫成天误工伺候她。这时“造反派”已经不当权了,“军宣队”才答应她和孩子回北京。丈夫却不让走。她回了北京,到协和医院去检查,原来竟是癌症,便打电报到向阳湖要她丈夫回去照顾。这边却只给了五天假。她丈夫回去了,写信来说明家里的困难病人已住院,医院里有事要和家属商量,孩子还太小,他要求再续假半个月。“军宣队”领导当即拍桌大怒,对刚刚“解放”当上排长的我说:“写信叫他回来!到底老婆重要,还是革命重要?”我只得遵命婉转一点照写了这封信,硬把她丈夫叫回来了。
下过这样的命令,我心里很不安。接着是自己的按例探亲假,我回到北京,就到协和医院去看了她,跟医生谈了谈。那女医生听说我是原单位的,就叹了口气,说:“人已经病到这样了,还不让家属来,哪个单位这样?你们这单位是怎么回事啊?”我当时不禁满脸通红,只能连声“嗯嗯”。这个大夫自然不会知道我们早已没单位了,跟没有妈的孩子差不多;她更不可能知道这个说不出话的我就是原单位已被打倒的负责人。我只能回到向阳湖,向“军宣队”领导委婉陈词加点谎话,说是协和大夫叫家属去的。不去,协和不答应。这才蒙领导恩准,让孙昌雯的丈夫回北京了。后来,孙昌雯总算由家人看着而死去。
第七个金人,这一位翻译家,本来并无什么罪状,在社里又和大部分群众水米无交。他所以作为“反革命”被揪下来,是由于“造反派”普查人们的历史,查出了他。当年原是共产党员,还是沈阳市的负责人。苏联部队和国民党部队进沈阳时,把他找出来,不知叫他公开办了个什么手续,这下子把党籍弄掉了。他自己对此从不隐讳,本无可斗,但是还是循例斗了,戴上帽子,赶到了向阳湖。他年龄既老,身体又坏,“造反派”手中没材料,本来就对他没多大兴趣,于是让他跟一群老弱病残一起去丹江。丹江是我们干校丧失劳动力的人的收容处,免了这群老弱病残的生产任务,却让他们自己种菜、打煤、做饭。中年人都不去。谁知道他们怎么干的?反正金人就死在那里了。
第八个是有名人物孟超。他本来是戏剧家,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是我们社主管戏剧的副总编辑。由于写了一本昆剧《李慧娘》更加出名。他曾经请我们全社去看戏。孟超的同乡康生曾极欣赏这个戏,有一次叫孟超陪着去钓鱼台演了一场,据说还请孟超吃了烤鸭。孟超回社都跟我们说过,当然颇为得意。真是想都想不到忽然冒出了个“有鬼无害论”事件,他竟变成了事件中的主要人物,说那个戏是影射党中央的,孟超写这戏是为了反党。康生首先翻脸拍案大怒,江青接着批示:“谁同意给这个反党分子提级的?就有阴谋,要追查。”我刚听说这事时,曾和孟超谈过一次。他说:“你想想,我怎么会反党,跟谁说谁能信的?但是竟然批下来了(真是侥幸,江青大约太忙,竟然没能查出这个首先同意他提级的人就是区区!后来我才知道那批语,怎禁得一身冷汗?)在“文革”前两年,孟超的名字已经不能见人了。到“文革”一爆发,他当然成了人所共知、全国共讨之的罪犯。开斗争会、来车把他押走时,一听说车上有他,连小孩子都在后头喊:“孟超,你是反革命不是?”他得连声答应:“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才罢休。
我是出版社“走资派”,但是孟超受的罪实在比我还多,还长久。我在戏剧上不通,听他的话,就是我“招降纳叛”的一大罪状。我不知道他这个正牌“降叛”该受了多少苦。
到向阳湖来改造,他当然是跑不掉的。我不知道他在这里共挨过多少次斗,反正他是长期的永久性的的斗争对象。到后来,其他的“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都算斗过做了结论,连我这样的“走资派”也算“解放”了。只有他却依然挂在那里。他病倒了,他的女儿由北京赶来侍病,军宣队恩准他去武汉治疗。治完了,没死,仍然叫回向阳湖来“改造”。到1972年底,我们这些干校学员大部分奉命返回北京原单位,他和少数“学员”依然在这里。直到1973年,这个干校终于算结束了,他才成了干校的末一班“毕业生”。回京以后不久,他就死了。他是悄悄地死去的,没有人追悼他,戏剧界也没有只字纪念文章。
第九位是外单位的了。中华书局的金灿然,他是老延安。在延安,我还是一个青年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在写书了。要知道,按延安的印刷条件,出书是非常困难的。当时我就见过他和叶蠖生合写的中国历史课本。到北京,他领导中华书局。除了学问比我这样初出茅庐的“领导干部”远为渊博之外,自有主见,有一套思想路子,很有办法,能大胆用人,多少位有用之才进了中华。每逢在一块儿开会,几个出版社的社领导都说该向他取经。可为了不知什么罪,他也被赶到向阳湖了。
中华这个连队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连队是邻居。我头一次突然碰见他,是见他与另一个老头子抬着一桶粪走过来,他见了我连头也没点,眼睛直直地就过去了。又见了几次,都是这个样子,好像不认识了,似乎是得了精神病。后来我才由我社的革命群众们口中听到,他连队有人对他作这样的评价:“金灿然那个老呆虫,成天就知道睡觉,还知道叫他抬粪,抬完粪就呼呼大睡。除了能抬抬粪,废物一个呗。”我不清楚金灿然是什么时候和怎么死的,只知道这个应该称为学者的人,就这样死了。
第十个,是我在北京早已熟识的作协评论家侯金镜。他们那连队也和我们连紧邻,我猜也猜得出侯金镜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最好的结果是当个小“走资派”或者“反动学术权威”,倒没猜出他也成了“现行反革命”。据说是因为闲谈中对林彪有不敬的言论,为此负罪来向阳湖,免不了常常挨斗。他本来是高血压,既为罪人,自然不能提到自己的病。他死的前一天,在地里干了活,回来洗脚入睡。据说情况并不变异,但是这个“罪犯”夜间不舒服,大约未敢惊动别人,天亮之后却不能动了。连队来人看他,已经不能言语。连队卫生员无法救治。看样子大概是突发脑溢血,送县医院早已来不及,他就死在他自己的卧床上,戴着罪名,一瞑不视。
这十个人永远逝去了。活人已经不大想起他们。至于他们为什么死的,也没有人再过问。虽然他们经历不同,有的是知名之士,有的是勤杂人员,但是他们的来路和结局却都是一样。我们一起被赶来的,不能一起走了。
人总是要死的。也许某人当时不死,如今也已太平地寿终。也许某人现在还活着,在和别人一样地提笔写文章,但是上面提的十个人,是在那个时候在向阳湖畔不甘心地告别人世的。我忘不了的向阳湖。流泪、沉痛都已毫无用处。我不想描画那些临死悲惨的场面,现在记下他们,只为的是让今天主事掌权的中年人即当年的孩子们,想起这些糊里糊涂送了命的叔叔阿姨。不该忘掉的,好好想想看,你们还想得起吗?